当第三人称遇上我 10000字
文章摘要:高三作文10000字:怎么写好当第三人称遇上我10000字作文?我不想去赘述他的容貌他的嗓音他的身形。他曾说过:“那些东西如身外浮云,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迫于此我也不便多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竟有些赞同他的话,这是在我看来所诡谲而不可思议的。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这所学校,这个班级里他的成绩不算太好,中游,甚至稍稍偏下。以下是叶放写的《当第三人称遇上我》范文;
好当第三人称遇上我作文10000字概况
- 作者:叶放
- 班级:高中高三
- 字数:10000字作文
- 体裁:
- 段落:分127段叙写
- 更新:2026年01月18日 17时39分
我不想去赘述他的容貌他的嗓音他的身形。他曾说过:“那些东西如身外浮云,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迫于此我也不便多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竟有些赞同他的话,这是在我看来所诡谲而不可思议的。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这所学校,这个班级里他的成绩不算太好,中游,甚至稍稍偏下。这是由于他对生活的态度。
他藐视一切学科。在数学课上写一些东西,在语文课上却又写起数学卷子来;在政治课上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却又在物理课上偷偷看哲学的东西。
他对生活像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即使回到宿舍也是寡言少语,倒头便睡。每天固定六点半起床,做好洗漱等,又在六点五十固定下楼,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有人批评他过得麻木而漠知,但也不便当面谈起,只与我说。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却暗自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怀磅礴大气的梦想,但最后也渐衰落。他对我批评现实的残忍与混乱,却总是轻描淡写而过,并不暴怒而起。
他爱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乘了火车,一路漂泊,去往一些未知的地域,或是与他同行者所去的彼岸。但他也很清楚,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于是他只能发泄于一些无用的东西,例如文字。他什么都写什么都记,上课时也喜欢观察台上老师的一举一动,然后再饶有兴趣地描述下来。他也写歌词,加了一个音乐才华者的群,在里面发自己的歌词。网友评论说他的歌词总太唯美,带一种沉静温和的生活态度,与这钢般的现实,竟有些格格不入。每当他听到这些时他总喜欢笑笑,却不说什么。我看过他的歌词,一篇名《夜色如海》,是些火车上旅者望窗外精致夜空时的温柔的诗句,确实带有一种平缓温和的感觉。我问他你自己搭过火车吗,他摇摇头,说他一次火车都没坐过。
这令我有些意外,人的想象力果然是无穷的。于是我又找他的东西看,发现他真有种疯子的感觉。当然这并非贬义,我也不知该如何说。他的文字在他的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感觉:有时张扬,有时内敛,但如今更多的还是温和。
其实既可以说温和,也可以说冷漠。他在他的一篇文字中指出,对他来说,温和冷漠麻木,其实是一样的。我虽然不敢苟同,却有些明白他的意思。这三个看来褒贬中三性的词语,都是他温和条件下的一种转化,是一种対及生活的态度。而我意外地发现他对自己也有一定了解,但过于偏执而极端。他近乎疯狂而虔诚地认为他自己拥有两个人格,在这之上又交错而成密密麻麻交织成无数人格碎片。我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他释放压力的一种错觉,但他仍信任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他同时爱上科幻,哲学,与精致的沉静的温和的文字这两种极端的唯一解释。
我却摇了摇头。他还在自顾自地说着他的两个性格总互相对立,谁也不让谁。
他爱听朴树的歌,却不喜如那些花儿或生如夏花等已被众人熟知的歌,只喜听偏僻冷门的。他曾告诉我他最爱的是且听风吟,内澈一种温柔如时光的美感。但他最近又告诉我他又爱上了另一首《九月》,不是太因为曲子,而是它的歌词。他说这如同我们,在这城市举措犹豫时,却又疯狂不定,像极了两个极端,我们就在这里游走。
他喜欢暗夜。——或者说,他爱这暗夜。常然是在深夜,他的舍友都睡着了,他却还未入睡,只是默默地坐在窗边,看窗外温红色的夜空,再想些片刻即忘的沉默片段。他告诉我即使在家里他也很晚睡,常常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电脑后是窗帘,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能遇见沉静的夜空——没有月光,没有星点,有的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感觉,犹如夜色的脉动,能从面前的死寂里传来。他坦言关于这暗夜他觉得他能从里面寻到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人们都沉睡了,只有他还醒着,用沉默的目光看这世界,看这无声的暗夜,竟有迷茫和清醒的双重感知。——霎时间我觉得一股寂寞和无言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这是一种探知和自悟。
记到这儿我又想起他的那篇《夜色如海》,里面是这么写的。
“一杯咖啡在深夜
散发沉静的香气
就像我又醒来时
听见的火车汽笛
车厢沉默而喧嚷
但是仿佛这一刻
听不见任何声音
犹如精致的夜空
当你朝窗外看去
车窗外云散星点
像是倦容和思念
这夜色犹如深海。”
他手上有一篇未完成的稿零我不想去赘述他的容貌他的嗓音他的身形。他曾说过:“那些东西如身外浮云,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迫于此我也不便多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竟有些赞同他的话,这是在我看来所诡谲而不可思议的。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这所学校,这个班级里他的成绩不算太好,中游,甚至稍稍偏下。这是由于他对生活的态度。
他藐视一切学科。在数学课上写一些东西,在语文课上却又写起数学卷子来;在政治课上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却又在物理课上偷偷看哲学的东西。
他对生活像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即使回到宿舍也是寡言少语,倒头便睡。每天固定六点半起床,做好洗漱等,又在六点五十固定下楼,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有人批评他过得麻木而漠知,但也不便当面谈起,只与我说。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却暗自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怀磅礴大气的梦想,但最后也渐衰落。他对我批评现实的残忍与混乱,却总是轻描淡写而过,并不暴怒而起。
他爱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乘了火车,一路漂泊,去往一些未知的地域,或是与他同行者所去的彼岸。但他也很清楚,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于是他只能发泄于一些无用的东西,例如文字。他什么都写什么都记,上课时也喜欢观察台上老师的一举一动,然后再饶有兴趣地描述下来。他也写歌词,加了一个音乐才华者的群,在里面发自己的歌词。网友评论说他的歌词总太唯美,带一种沉静温和的生活态度,与这钢般的现实,竟有些格格不入。每当他听到这些时他总喜欢笑笑,却不说什么。我看过他的歌词,一篇名《夜色如海》,是些火车上旅者望窗外精致夜空时的温柔的诗句,确实带有一种平缓温和的感觉。我问他你自己搭过火车吗,他摇摇头,说他一次火车都没坐过。
这令我有些意外,人的想象力果然是无穷的。于是我又找他的东西看,发现他真有种疯子的感觉。当然这并非贬义,我也不知该如何说。他的文字在他的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感觉:有时张扬,有时内敛,但如今更多的还是温和。
其实既可以说温和,也可以说冷漠。他在他的一篇文字中指出,对他来说,温和冷漠麻木,其实是一样的。我虽然不敢苟同,却有些明白他的意思。这三个看来褒贬中三性的词语,都是他温和条件下的一种转化,是一种対及生活的态度。而我意外地发现他对自己也有一定了解,但过于偏执而极端。他近乎疯狂而虔诚地认为他自己拥有两个人格,在这之上又交错而成密密麻麻交织成无数人格碎片。我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他释放压力的一种错觉,但他仍信任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他同时爱上科幻,哲学,与精致的沉静的温和的文字这两种极端的唯一解释。
我却摇了摇头。他还在自顾自地说着他的两个性格总互相对立,谁也不让谁。
他爱听朴树的歌,却不喜如那些花儿或生如夏花等已被众人熟知的歌,只喜听偏僻冷门的。他曾告诉我他最爱的是且听风吟,内澈一种温柔如时光的美感。但他最近又告诉我他又爱上了另一首《九月》,不是太因为曲子,而是它的歌词。他说这如同我们,在这城市举措犹豫时,却又疯狂不定,像极了两个极端,我们就在这里游走。
他喜欢暗夜。——或者说,他爱这暗夜。常然是在深夜,他的舍友都睡着了,他却还未入睡,只是默默地坐在窗边,看窗外温红色的夜空,再想些片刻即忘的沉默片段。他告诉我即使在家里他也很晚睡,常常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电脑后是窗帘,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能遇见沉静的夜空——没有月光,没有星点,有的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感觉,犹如夜色的脉动,能从面前的死寂里传来。他坦言关于这暗夜他觉得他能从里面寻到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人们都沉睡了,只有他还醒着,用沉默的目光看这世界,看这无声的暗夜,竟有迷茫和清醒的双重感知。——霎时间我觉得一股寂寞和无言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这是一种探知和自悟。
记到这儿我又想起他的那篇《夜色如海》,里面是这么写的。
“一杯咖啡在深夜
散发沉静的香气
就像我又醒来时
听见的火车汽笛
车厢沉默而喧嚷
但是仿佛这一刻
听不见任何声音
犹如精致的夜空
当你朝窗外看去
车窗外云散星点
像是倦容和思念
这夜色犹如深海。”
他手上有一篇未完成的稿零我不想去赘述他的容貌他的嗓音他的身形。他曾说过:“那些东西如身外浮云,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迫于此我也不便多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竟有些赞同他的话,这是在我看来所诡谲而不可思议的。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这所学校,这个班级里他的成绩不算太好,中游,甚至稍稍偏下。这是由于他对生活的态度。
他藐视一切学科。在数学课上写一些东西,在语文课上却又写起数学卷子来;在政治课上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却又在物理课上偷偷看哲学的东西。
他对生活像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即使回到宿舍也是寡言少语,倒头便睡。每天固定六点半起床,做好洗漱等,又在六点五十固定下楼,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有人批评他过得麻木而漠知,但也不便当面谈起,只与我说。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却暗自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怀磅礴大气的梦想,但最后也渐衰落。他对我批评现实的残忍与混乱,却总是轻描淡写而过,并不暴怒而起。
他爱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乘了火车,一路漂泊,去往一些未知的地域,或是与他同行者所去的彼岸。但他也很清楚,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于是他只能发泄于一些无用的东西,例如文字。他什么都写什么都记,上课时也喜欢观察台上老师的一举一动,然后再饶有兴趣地描述下来。他也写歌词,加了一个音乐才华者的群,在里面发自己的歌词。网友评论说他的歌词总太唯美,带一种沉静温和的生活态度,与这钢般的现实,竟有些格格不入。每当他听到这些时他总喜欢笑笑,却不说什么。我看过他的歌词,一篇名《夜色如海》,是些火车上旅者望窗外精致夜空时的温柔的诗句,确实带有一种平缓温和的感觉。我问他你自己搭过火车吗,他摇摇头,说他一次火车都没坐过。
这令我有些意外,人的想象力果然是无穷的。于是我又找他的东西看,发现他真有种疯子的感觉。当然这并非贬义,我也不知该如何说。他的文字在他的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感觉:有时张扬,有时内敛,但如今更多的还是温和。
其实既可以说温和,也可以说冷漠。他在他的一篇文字中指出,对他来说,温和冷漠麻木,其实是一样的。我虽然不敢苟同,却有些明白他的意思。这三个看来褒贬中三性的词语,都是他温和条件下的一种转化,是一种対及生活的态度。而我意外地发现他对自己也有一定了解,但过于偏执而极端。他近乎疯狂而虔诚地认为他自己拥有两个人格,在这之上又交错而成密密麻麻交织成无数人格碎片。我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他释放压力的一种错觉,但他仍信任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他同时爱上科幻,哲学,与精致的沉静的温和的文字这两种极端的唯一解释。
我却摇了摇头。他还在自顾自地说着他的两个性格总互相对立,谁也不让谁。
他爱听朴树的歌,却不喜如那些花儿或生如夏花等已被众人熟知的歌,只喜听偏僻冷门的。他曾告诉我他最爱的是且听风吟,内澈一种温柔如时光的美感。但他最近又告诉我他又爱上了另一首《九月》,不是太因为曲子,而是它的歌词。他说这如同我们,在这城市举措犹豫时,却又疯狂不定,像极了两个极端,我们就在这里游走。
他喜欢暗夜。——或者说,他爱这暗夜。常然是在深夜,他的舍友都睡着了,他却还未入睡,只是默默地坐在窗边,看窗外温红色的夜空,再想些片刻即忘的沉默片段。他告诉我即使在家里他也很晚睡,常常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电脑后是窗帘,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能遇见沉静的夜空——没有月光,没有星点,有的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感觉,犹如夜色的脉动,能从面前的死寂里传来。他坦言关于这暗夜他觉得他能从里面寻到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人们都沉睡了,只有他还醒着,用沉默的目光看这世界,看这无声的暗夜,竟有迷茫和清醒的双重感知。——霎时间我觉得一股寂寞和无言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这是一种探知和自悟。
记到这儿我又想起他的那篇《夜色如海》,里面是这么写的。
“一杯咖啡在深夜
散发沉静的香气
就像我又醒来时
听见的火车汽笛
车厢沉默而喧嚷
但是仿佛这一刻
听不见任何声音
犹如精致的夜空
当你朝窗外看去
车窗外云散星点
像是倦容和思念
这夜色犹如深海。”
他手上有一篇未完成的稿零我不想去赘述他的容貌他的嗓音他的身形。他曾说过:“那些东西如身外浮云,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迫于此我也不便多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竟有些赞同他的话,这是在我看来所诡谲而不可思议的。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这所学校,这个班级里他的成绩不算太好,中游,甚至稍稍偏下。这是由于他对生活的态度。
他藐视一切学科。在数学课上写一些东西,在语文课上却又写起数学卷子来;在政治课上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却又在物理课上偷偷看哲学的东西。
他对生活像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即使回到宿舍也是寡言少语,倒头便睡。每天固定六点半起床,做好洗漱等,又在六点五十固定下楼,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有人批评他过得麻木而漠知,但也不便当面谈起,只与我说。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却暗自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怀磅礴大气的梦想,但最后也渐衰落。他对我批评现实的残忍与混乱,却总是轻描淡写而过,并不暴怒而起。
他爱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乘了火车,一路漂泊,去往一些未知的地域,或是与他同行者所去的彼岸。但他也很清楚,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于是他只能发泄于一些无用的东西,例如文字。他什么都写什么都记,上课时也喜欢观察台上老师的一举一动,然后再饶有兴趣地描述下来。他也写歌词,加了一个音乐才华者的群,在里面发自己的歌词。网友评论说他的歌词总太唯美,带一种沉静温和的生活态度,与这钢般的现实,竟有些格格不入。每当他听到这些时他总喜欢笑笑,却不说什么。我看过他的歌词,一篇名《夜色如海》,是些火车上旅者望窗外精致夜空时的温柔的诗句,确实带有一种平缓温和的感觉。我问他你自己搭过火车吗,他摇摇头,说他一次火车都没坐过。
这令我有些意外,人的想象力果然是无穷的。于是我又找他的东西看,发现他真有种疯子的感觉。当然这并非贬义,我也不知该如何说。他的文字在他的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感觉:有时张扬,有时内敛,但如今更多的还是温和。
其实既可以说温和,也可以说冷漠。他在他的一篇文字中指出,对他来说,温和冷漠麻木,其实是一样的。我虽然不敢苟同,却有些明白他的意思。这三个看来褒贬中三性的词语,都是他温和条件下的一种转化,是一种対及生活的态度。而我意外地发现他对自己也有一定了解,但过于偏执而极端。他近乎疯狂而虔诚地认为他自己拥有两个人格,在这之上又交错而成密密麻麻交织成无数人格碎片。我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他释放压力的一种错觉,但他仍信任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他同时爱上科幻,哲学,与精致的沉静的温和的文字这两种极端的唯一解释。
我却摇了摇头。他还在自顾自地说着他的两个性格总互相对立,谁也不让谁。
他爱听朴树的歌,却不喜如那些花儿或生如夏花等已被众人熟知的歌,只喜听偏僻冷门的。他曾告诉我他最爱的是且听风吟,内澈一种温柔如时光的美感。但他最近又告诉我他又爱上了另一首《九月》,不是太因为曲子,而是它的歌词。他说这如同我们,在这城市举措犹豫时,却又疯狂不定,像极了两个极端,我们就在这里游走。
他喜欢暗夜。——或者说,他爱这暗夜。常然是在深夜,他的舍友都睡着了,他却还未入睡,只是默默地坐在窗边,看窗外温红色的夜空,再想些片刻即忘的沉默片段。他告诉我即使在家里他也很晚睡,常常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电脑后是窗帘,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能遇见沉静的夜空——没有月光,没有星点,有的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感觉,犹如夜色的脉动,能从面前的死寂里传来。他坦言关于这暗夜他觉得他能从里面寻到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人们都沉睡了,只有他还醒着,用沉默的目光看这世界,看这无声的暗夜,竟有迷茫和清醒的双重感知。——霎时间我觉得一股寂寞和无言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这是一种探知和自悟。
记到这儿我又想起他的那篇《夜色如海》,里面是这么写的。
“一杯咖啡在深夜
散发沉静的香气
就像我又醒来时
听见的火车汽笛
车厢沉默而喧嚷
但是仿佛这一刻
听不见任何声音
犹如精致的夜空
当你朝窗外看去
车窗外云散星点
像是倦容和思念
这夜色犹如深海。”
他手上有一篇未完成的稿零我不想去赘述他的容貌他的嗓音他的身形。他曾说过:“那些东西如身外浮云,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迫于此我也不便多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竟有些赞同他的话,这是在我看来所诡谲而不可思议的。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这所学校,这个班级里他的成绩不算太好,中游,甚至稍稍偏下。这是由于他对生活的态度。
他藐视一切学科。在数学课上写一些东西,在语文课上却又写起数学卷子来;在政治课上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却又在物理课上偷偷看哲学的东西。
他对生活像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即使回到宿舍也是寡言少语,倒头便睡。每天固定六点半起床,做好洗漱等,又在六点五十固定下楼,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有人批评他过得麻木而漠知,但也不便当面谈起,只与我说。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却暗自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怀磅礴大气的梦想,但最后也渐衰落。他对我批评现实的残忍与混乱,却总是轻描淡写而过,并不暴怒而起。
他爱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乘了火车,一路漂泊,去往一些未知的地域,或是与他同行者所去的彼岸。但他也很清楚,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于是他只能发泄于一些无用的东西,例如文字。他什么都写什么都记,上课时也喜欢观察台上老师的一举一动,然后再饶有兴趣地描述下来。他也写歌词,加了一个音乐才华者的群,在里面发自己的歌词。网友评论说他的歌词总太唯美,带一种沉静温和的生活态度,与这钢般的现实,竟有些格格不入。每当他听到这些时他总喜欢笑笑,却不说什么。我看过他的歌词,一篇名《夜色如海》,是些火车上旅者望窗外精致夜空时的温柔的诗句,确实带有一种平缓温和的感觉。我问他你自己搭过火车吗,他摇摇头,说他一次火车都没坐过。
这令我有些意外,人的想象力果然是无穷的。于是我又找他的东西看,发现他真有种疯子的感觉。当然这并非贬义,我也不知该如何说。他的文字在他的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感觉:有时张扬,有时内敛,但如今更多的还是温和。
其实既可以说温和,也可以说冷漠。他在他的一篇文字中指出,对他来说,温和冷漠麻木,其实是一样的。我虽然不敢苟同,却有些明白他的意思。这三个看来褒贬中三性的词语,都是他温和条件下的一种转化,是一种対及生活的态度。而我意外地发现他对自己也有一定了解,但过于偏执而极端。他近乎疯狂而虔诚地认为他自己拥有两个人格,在这之上又交错而成密密麻麻交织成无数人格碎片。我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他释放压力的一种错觉,但他仍信任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他同时爱上科幻,哲学,与精致的沉静的温和的文字这两种极端的唯一解释。
我却摇了摇头。他还在自顾自地说着他的两个性格总互相对立,谁也不让谁。
他爱听朴树的歌,却不喜如那些花儿或生如夏花等已被众人熟知的歌,只喜听偏僻冷门的。他曾告诉我他最爱的是且听风吟,内澈一种温柔如时光的美感。但他最近又告诉我他又爱上了另一首《九月》,不是太因为曲子,而是它的歌词。他说这如同我们,在这城市举措犹豫时,却又疯狂不定,像极了两个极端,我们就在这里游走。
他喜欢暗夜。——或者说,他爱这暗夜。常然是在深夜,他的舍友都睡着了,他却还未入睡,只是默默地坐在窗边,看窗外温红色的夜空,再想些片刻即忘的沉默片段。他告诉我即使在家里他也很晚睡,常常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电脑后是窗帘,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能遇见沉静的夜空——没有月光,没有星点,有的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感觉,犹如夜色的脉动,能从面前的死寂里传来。他坦言关于这暗夜他觉得他能从里面寻到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人们都沉睡了,只有他还醒着,用沉默的目光看这世界,看这无声的暗夜,竟有迷茫和清醒的双重感知。——霎时间我觉得一股寂寞和无言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这是一种探知和自悟。
记到这儿我又想起他的那篇《夜色如海》,里面是这么写的。
“一杯咖啡在深夜
散发沉静的香气
就像我又醒来时
听见的火车汽笛
车厢沉默而喧嚷
但是仿佛这一刻
听不见任何声音
犹如精致的夜空
当你朝窗外看去
车窗外云散星点
像是倦容和思念
这夜色犹如深海。”
他手上有一篇未完成的稿零我不想去赘述他的容貌他的嗓音他的身形。他曾说过:“那些东西如身外浮云,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迫于此我也不便多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竟有些赞同他的话,这是在我看来所诡谲而不可思议的。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这所学校,这个班级里他的成绩不算太好,中游,甚至稍稍偏下。这是由于他对生活的态度。
他藐视一切学科。在数学课上写一些东西,在语文课上却又写起数学卷子来;在政治课上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却又在物理课上偷偷看哲学的东西。
他对生活像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即使回到宿舍也是寡言少语,倒头便睡。每天固定六点半起床,做好洗漱等,又在六点五十固定下楼,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有人批评他过得麻木而漠知,但也不便当面谈起,只与我说。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却暗自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怀磅礴大气的梦想,但最后也渐衰落。他对我批评现实的残忍与混乱,却总是轻描淡写而过,并不暴怒而起。
他爱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乘了火车,一路漂泊,去往一些未知的地域,或是与他同行者所去的彼岸。但他也很清楚,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于是他只能发泄于一些无用的东西,例如文字。他什么都写什么都记,上课时也喜欢观察台上老师的一举一动,然后再饶有兴趣地描述下来。他也写歌词,加了一个音乐才华者的群,在里面发自己的歌词。网友评论说他的歌词总太唯美,带一种沉静温和的生活态度,与这钢般的现实,竟有些格格不入。每当他听到这些时他总喜欢笑笑,却不说什么。我看过他的歌词,一篇名《夜色如海》,是些火车上旅者望窗外精致夜空时的温柔的诗句,确实带有一种平缓温和的感觉。我问他你自己搭过火车吗,他摇摇头,说他一次火车都没坐过。
这令我有些意外,人的想象力果然是无穷的。于是我又找他的东西看,发现他真有种疯子的感觉。当然这并非贬义,我也不知该如何说。他的文字在他的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感觉:有时张扬,有时内敛,但如今更多的还是温和。
其实既可以说温和,也可以说冷漠。他在他的一篇文字中指出,对他来说,温和冷漠麻木,其实是一样的。我虽然不敢苟同,却有些明白他的意思。这三个看来褒贬中三性的词语,都是他温和条件下的一种转化,是一种対及生活的态度。而我意外地发现他对自己也有一定了解,但过于偏执而极端。他近乎疯狂而虔诚地认为他自己拥有两个人格,在这之上又交错而成密密麻麻交织成无数人格碎片。我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他释放压力的一种错觉,但他仍信任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他同时爱上科幻,哲学,与精致的沉静的温和的文字这两种极端的唯一解释。
我却摇了摇头。他还在自顾自地说着他的两个性格总互相对立,谁也不让谁。
他爱听朴树的歌,却不喜如那些花儿或生如夏花等已被众人熟知的歌,只喜听偏僻冷门的。他曾告诉我他最爱的是且听风吟,内澈一种温柔如时光的美感。但他最近又告诉我他又爱上了另一首《九月》,不是太因为曲子,而是它的歌词。他说这如同我们,在这城市举措犹豫时,却又疯狂不定,像极了两个极端,我们就在这里游走。
他喜欢暗夜。——或者说,他爱这暗夜。常然是在深夜,他的舍友都睡着了,他却还未入睡,只是默默地坐在窗边,看窗外温红色的夜空,再想些片刻即忘的沉默片段。他告诉我即使在家里他也很晚睡,常常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电脑后是窗帘,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能遇见沉静的夜空——没有月光,没有星点,有的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感觉,犹如夜色的脉动,能从面前的死寂里传来。他坦言关于这暗夜他觉得他能从里面寻到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人们都沉睡了,只有他还醒着,用沉默的目光看这世界,看这无声的暗夜,竟有迷茫和清醒的双重感知。——霎时间我觉得一股寂寞和无言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这是一种探知和自悟。
记到这儿我又想起他的那篇《夜色如海》,里面是这么写的。
“一杯咖啡在深夜
散发沉静的香气
就像我又醒来时
听见的火车汽笛
车厢沉默而喧嚷
但是仿佛这一刻
听不见任何声音
犹如精致的夜空
当你朝窗外看去
车窗外云散星点
像是倦容和思念
这夜色犹如深海。”
他手上有一篇未完成的稿零我不想去赘述他的容貌他的嗓音他的身形。他曾说过:“那些东西如身外浮云,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迫于此我也不便多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竟有些赞同他的话,这是在我看来所诡谲而不可思议的。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这所学校,这个班级里他的成绩不算太好,中游,甚至稍稍偏下。这是由于他对生活的态度。
他藐视一切学科。在数学课上写一些东西,在语文课上却又写起数学卷子来;在政治课上旁若无人地呼呼大睡,却又在物理课上偷偷看哲学的东西。
他对生活像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即使回到宿舍也是寡言少语,倒头便睡。每天固定六点半起床,做好洗漱等,又在六点五十固定下楼,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有人批评他过得麻木而漠知,但也不便当面谈起,只与我说。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却暗自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怀磅礴大气的梦想,但最后也渐衰落。他对我批评现实的残忍与混乱,却总是轻描淡写而过,并不暴怒而起。
他爱写些东西。他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乘了火车,一路漂泊,去往一些未知的地域,或是与他同行者所去的彼岸。但他也很清楚,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于是他只能发泄于一些无用的东西,例如文字。他什么都写什么都记,上课时也喜欢观察台上老师的一举一动,然后再饶有兴趣地描述下来。他也写歌词,加了一个音乐才华者的群,在里面发自己的歌词。网友评论说他的歌词总太唯美,带一种沉静温和的生活态度,与这钢般的现实,竟有些格格不入。每当他听到这些时他总喜欢笑笑,却不说什么。我看过他的歌词,一篇名《夜色如海》,是些火车上旅者望窗外精致夜空时的温柔的诗句,确实带有一种平缓温和的感觉。我问他你自己搭过火车吗,他摇摇头,说他一次火车都没坐过。
这令我有些意外,人的想象力果然是无穷的。于是我又找他的东西看,发现他真有种疯子的感觉。当然这并非贬义,我也不知该如何说。他的文字在他的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感觉:有时张扬,有时内敛,但如今更多的还是温和。
其实既可以说温和,也可以说冷漠。他在他的一篇文字中指出,对他来说,温和冷漠麻木,其实是一样的。我虽然不敢苟同,却有些明白他的意思。这三个看来褒贬中三性的词语,都是他温和条件下的一种转化,是一种対及生活的态度。而我意外地发现他对自己也有一定了解,但过于偏执而极端。他近乎疯狂而虔诚地认为他自己拥有两个人格,在这之上又交错而成密密麻麻交织成无数人格碎片。我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他释放压力的一种错觉,但他仍信任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他同时爱上科幻,哲学,与精致的沉静的温和的文字这两种极端的唯一解释。
我却摇了摇头。他还在自顾自地说着他的两个性格总互相对立,谁也不让谁。
他爱听朴树的歌,却不喜如那些花儿或生如夏花等已被众人熟知的歌,只喜听偏僻冷门的。他曾告诉我他最爱的是且听风吟,内澈一种温柔如时光的美感。但他最近又告诉我他又爱上了另一首《九月》,不是太因为曲子,而是它的歌词。他说这如同我们,在这城市举措犹豫时,却又疯狂不定,像极了两个极端,我们就在这里游走。
他喜欢暗夜。——或者说,他爱这暗夜。常然是在深夜,他的舍友都睡着了,他却还未入睡,只是默默地坐在窗边,看窗外温红色的夜空,再想些片刻即忘的沉默片段。他告诉我即使在家里他也很晚睡,常常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电脑后是窗帘,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能遇见沉静的夜空——没有月光,没有星点,有的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感觉,犹如夜色的脉动,能从面前的死寂里传来。他坦言关于这暗夜他觉得他能从里面寻到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人们都沉睡了,只有他还醒着,用沉默的目光看这世界,看这无声的暗夜,竟有迷茫和清醒的双重感知。——霎时间我觉得一股寂寞和无言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这是一种探知和自悟。
记到这儿我又想起他的那篇《夜色如海》,里面是这么写的。
“一杯咖啡在深夜
散发沉静的香气
就像我又醒来时
听见的火车汽笛
车厢沉默而喧嚷
但是仿佛这一刻
听不见任何声音
犹如精致的夜空
当你朝窗外看去
车窗外云散星点
像是倦容和思念
这夜色犹如深海。”
他手上有一篇未完成的稿

好文章,赞一下
991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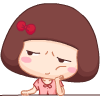
很一般,需努力
5091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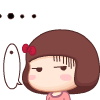
太差劲,踩一下
80人
- 上一篇:非90后作文450字
- 下一篇:QQ三国战例作文350字